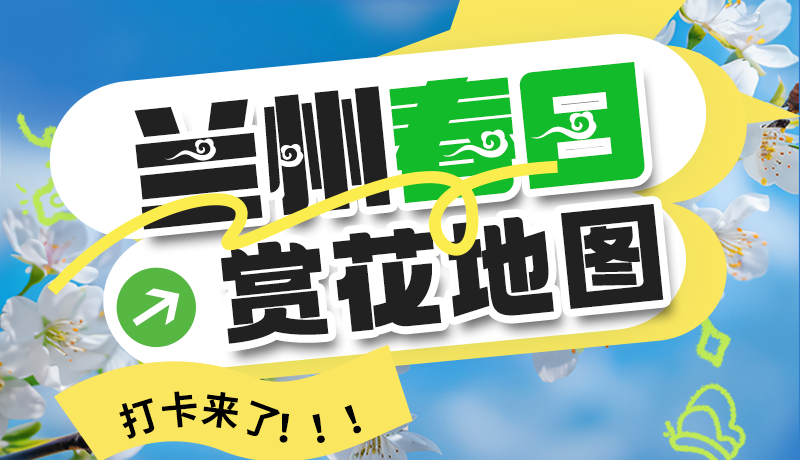原標題:事故發生后駕車離開又返回,算逃逸嗎?
受邀嘉賓:甘肅策橫律師事務所律師阮 磊
主持人:新甘肅·甘肅法治報記者李曉云
本期主題:近年來,隨著機動車保有量激增,交通事故的發生也在所難免。部分駕駛人在事故后因恐慌、逃避責任等原因短暫離開現場,事后又主動返回處理,此類行為是否構成法律意義上的“逃逸”?本期“舉案說法”將結合典型案例,剖析交通肇事逃逸的認定標準,厘清影響量刑的因素,為公眾提供明晰的法律指引。
典型案例:2023年2月23日,被告人李某某駕駛一輛小型普通客車行駛時,與在道路上的被害人岑某某發生碰撞,造成岑某某不幸身亡、車輛損壞的交通事故。事故發生后,李某某駕車逃離現場,前往某村找其丈夫梁某某,隨后李某某撥打了110、120電話,并與梁某某一同返回到事故現場。經認定,李某某承擔事故全部責任,岑某某無責任。經鑒定,岑某某系道路交通事故導致顱腦損傷死亡。案發后,被告人李某某及車輛保險公司共同賠償了被害人家屬經濟損失共計22.57萬余元。
裁判結果: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李某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且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其行為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構成交通肇事。依法應當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被告人李某某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且自愿認罪認罰,依法可以減輕處罰。同時,被告人李某某及車輛保險公司賠償了被害人家屬的經濟損失,可以酌情從輕處罰。綜合以上,判決被告人李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八個月。
主持人:交通肇事后“逃逸”如何認定?
阮 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及相關司法解釋,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核心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目的,而非單純物理上離開現場。即使肇事者事后返回或賠償,也不影響“逃逸”的成立,只要其離開時存在逃避責任的故意。本案中,李某某在事故發生后未履行法定義務(如保護現場、救助傷者、報警),而是直接駕車離開現場前往他處尋求丈夫幫助,客觀上已構成脫離事故現場的行為,延誤了救治時機,且無證據證明其離開系因緊急避險或合理事由。盡管其后續主動撥打報警電話并返回,但李某某離開時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已經阻斷了及時救助及事故處理。因此,李某某的行為符合“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法定情形,構成“逃逸”加重情節。
主持人:自首與認罪認罰如何影響交通肇事罪的量刑?
阮 磊:自首與認罪認罰是法定從寬量刑情節,但二者適用需符合嚴格條件。本案中,李某某在離開現場后主動撥打110報警,屬于“自動投案”;到案后如實供述事故經過,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如實供述”的要求,構成自首,依法可減輕處罰。此外,李某某在審判階段自愿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可進一步從寬處理,結合其賠償被害人親屬經濟損失的情節,法院最終在“逃逸”加重情節的法定刑基礎上,將刑期降至二年八個月。也就是說,自首與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受案件性質和社會危害性的影響。本案中,李某某雖因“逃逸”面臨3年以上刑罰,但因自首、認罪認罰、賠償等情節疊加,才會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主持人:民事賠償能否完全抵消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責任?
阮 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民事賠償屬于“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即賠償損失可影響量刑,但不能免除刑事責任。交通肇事罪侵害的是公共安全法益,賠償僅彌補經濟損失,無法消除行為對生命權的剝奪和社會秩序的破壞。同時,賠償也需要體現“充分性”和“主動性”。若賠償金額顯著低于實際損失,或拖延至審判階段才支付,法院可能不予從輕。本案中,李某某的賠償行為雖無法免除刑罰,但結合自首、認罪認罰等情節,成為了降低刑期至二年八個月的重要因素。民事賠償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手段,但不能“以賠代刑”;積極賠償與認罪悔罪相結合,方能在法律框架內爭取最優結果。
- 2025-04-03護航春耕路 筑牢安全線
- 2025-04-03寧縣政法委組織開展“平安法治護春耕”主題行動
- 2025-03-17成縣司法局為群眾送上消費維權“大禮包”
- 2025-03-17白銀檢察開展誠信主題宣傳活動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