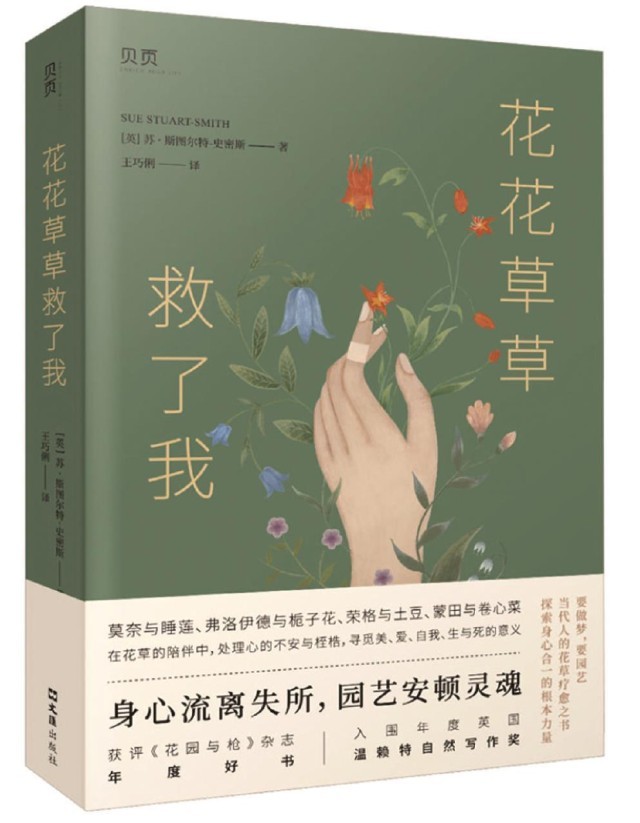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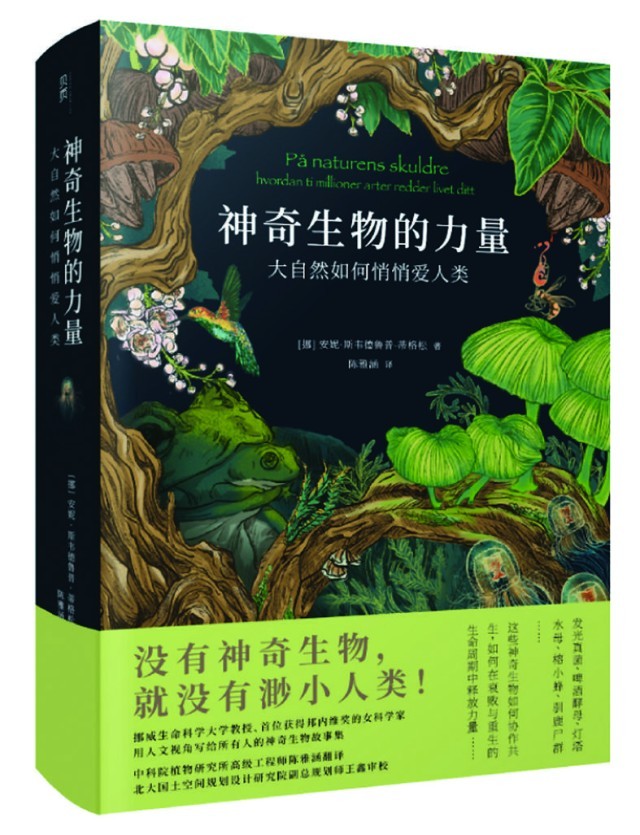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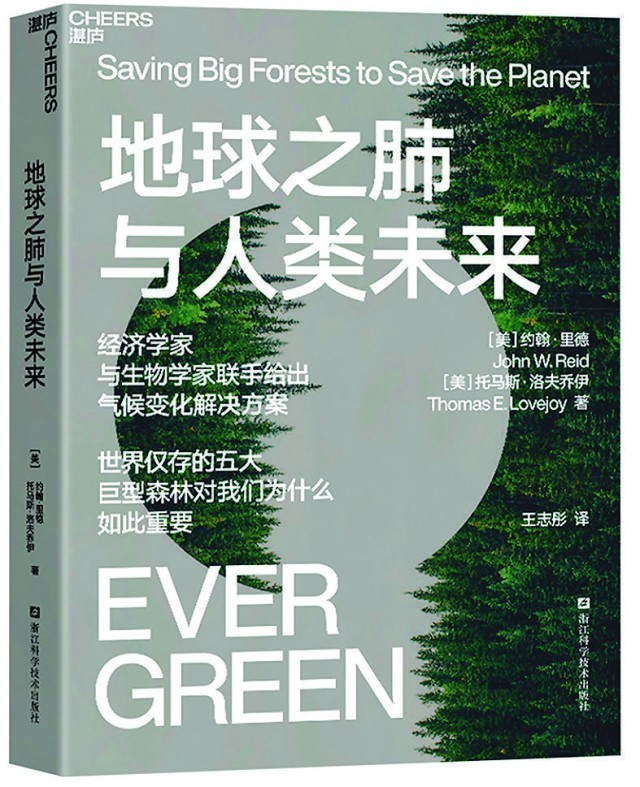
《花花草草救了我》 [英]蘇·斯圖爾特-史密斯著 王巧俐 譯 文匯出版社出版
■徐海清
花花草草是否可能救人一命?生物物種多樣性有多么重要?為什么要保護好森林、尤其是巨型森林?這些也許都是很日常、并非十分深奧的問題。然而,對一種現象的了解不等于能自然而然地深入理解之,只有理解了它發生、存在的原理、內在邏輯,才能更深切地了解之。筆者讀了三本科普譯著,從實踐與理論兩個層面體會和理解園藝、綠植與人類身心健康、社會發展的關系,驚嘆于生物力量的神奇,提升了親近大自然的自覺。
園藝療愈下的長壽奇跡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及達達尼爾海峽地區打了近一年的海戰與登陸戰,極為慘烈。1915年春,英法16艘戰艦初探達達尼爾海峽。期間,英國皇家海軍一艘潛艇在海峽擱淺,大部分士兵被俘送進了“勞動營”。相信一戰史著述都會對這次大規模戰役有所述評,但不知有否對這批被俘士兵的下落花些筆墨。孰料百余年后,當年一名戰俘的外孫女在其科普著作《花花草草救了我》中講述了外祖父的傳奇經歷:他從海路逃出勞動營,在海上漂泊,靠飲水生存,最終獲救并在英國醫療船上得到初步治療。當他經陸路回到老家與未婚妻團聚時,原先精壯的小伙體重僅30多公斤,體檢診斷他只能活幾個月。幸有未婚妻不離不棄地照料,幾個月后命是保住了,但戰俘營經歷留下的恐懼心理卻如影隨形。能否好好活下去,是個嚴峻的問題。不久,他參加了一個園藝課程,后來夫妻倆買了一塊地,種植花卉蔬果,養豬養雞養蜂。他竟又健康地活了50多年,長壽的奇跡被認為是得益于園藝與農活、走進大自然療愈的結果。
《花花草草救了我》一書曾入圍英國自然與旅行寫作最高獎——溫賴特文學獎。作者蘇·斯圖爾特-史密斯,是醫生出身的精神病學家、熱衷于園藝的心理治療師。
一般情況下,園藝并非與救命相關聯,書中講述的各式各樣故事,更多是說明園藝可以療愈精神創傷。如紐約園藝學會與紐約市懲教局、教育局有一個合作項目,計劃每年為400名男女提供學習栽培和照顧植物的機會,這給他們帶來了希望和動力,使他們在離開里克斯島(世界上最大的監獄聚集區之一)后,絕大部分人沒有再次犯罪。這被認為在過去幾十年里最有說服力的一個園藝可以改善情緒、提高自尊、有助于緩解抑郁和焦慮的案例。
作者坦陳她本人在求學從業的道路上遇到困境時,也曾通過養花植樹來療愈自身。她匿名采訪過世界各地的囚犯、社區負責人和受過創傷的退伍軍人,梳理歷史名人與花花草草之間的故事,以親歷與大量調研所得的不同類型案例為依據,運用植物學、神經學、生理學、心理學、精神分析等領域的科學原理,揭示花花草草“撩撥或撫慰人心”的秘密,綜合解讀園藝的療愈、養生功能。
植物的繁盛與人類的繁榮之間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聯系。古往今來,在東西方,花園都被當作可為人們提供一個遠離世界喧囂和內心動蕩的庇護所。人類文明伊始,植物就影響了人類對生死的理解:年復一年的春去春來、花落花開、榮枯交替,讓我們覺得美好的一切會一直存在。這就是“花園帶給我們的永恒慰藉”。
“時空醫學”:常常到戶外去
人到中年,往往會感慨人生苦短,甚至產生死亡漸近之感。美國發展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森認為,中年時期也會感受到創造力的迸發,這種現象稱為“繁殖感”(“繁衍感”)。發展心理學所謂的“繁殖感”,不僅指繁殖下一代的需要,還指通過創造性的活動造福于下一代所帶來的體驗,這里是指后者。精神病學家喬治·維蘭特在《優雅地老去》一書中寫道:應對生活帶來的逆境,主要途徑之一是有“繁殖感”,要有各種“創意游戲”。方法很多,園藝無疑是其中之一。
作者把園藝演繹為一門“時空醫學”:戶外活動有助于拓展心靈空間,植物生長周期可以改變我們與時間的關系。“花園給了你一個受保護的物理空間,有助于增強你的心理空間感;花園也給了你一份平靜,因此你可以聆聽自己的心聲。”
1950年代以降,新型特效藥的使用改變了精神疾病的治療方法,新建醫院戶外綠地變得很少了。在作者看來,城市生活破壞人們健康的一面,首先表現為焦慮癥和抑郁癥帶來的危害。她引用上世紀著名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榮格的一個說法:現代生活中人們飽受“無根之痛”,因為城市居民不再有機會與大地連接。
到戶外去,也是《地球之肺與人類未來》倡導的理念。該書作者,美國的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經濟學家約翰·里德和被譽為“生物多樣性之父”的環保主義者托馬斯·洛夫喬伊寫道:常常到戶外去,哪怕只是找一片葉子,看看它的“葉脈三角洲”,也會讓你心馳神往。有些樹木,即使是一小簇,“也能釋放出單萜類物質來幫你減壓、降低你的血壓和心率……”(單萜類化合物具有令人愉快的氣味,是精油的主要成分)。
挪威生命科學大學教授、挪威自然研究所科學顧問、著有多部科普暢銷書的女科學家安妮·斯韋德魯普-蒂格松的《神奇生物的力量:大自然如何悄悄愛人類》中“宅人——自然與健康”一節,提及2008年英國的《每日郵報》有篇文章就1926年曾祖父開始的四代人中八歲兒童擁有的戶外活動的“權利”做了對比,結論是每況愈下;成年人大多數也過著“宅人”生活。遠離大自然會導致我們生病。反之,經常與土壤、植物和動物接觸,有助于建立免疫系統。長期活躍在綠色環境中還是防治心理健康問題的有效措施。
人類的食之源和大“藥房”
蒂格松指出:人類“都被編織進了大自然的經緯之中”,“沒有大自然來支撐我們,我們的文明就會衰落”。在植物范圍內怎樣解析如此宏大的題目呢?
首先,人類所食大部分屬于植物界,牛羊吃草的莖和葉,而我們吃草的后代——種子。植物還是其他所有生命的基礎,“人類不能基于無生命的化學物質(例如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我們吃的食物”,而植物可以通過光合作用,將它們合成為有機分子。
人類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續還得益于植物是一個“貨源充足”的無比碩大的“藥房”。蒂格松這本2021年面世的著作,及時地讓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創制的新型抗瘧疾藥物青蒿素在書中占有一席之地。提取青蒿素的物種其中文學名為黃花蒿,屠呦呦及其團隊在長期研究中,不僅發現了黃花蒿這種植物“含有有趣的活性成分”,更關鍵的是,他們發明了“從這種植物中提取活性物質的重要技巧”。
其次,蒂格松從物種多樣性角度進一步講述了植物作為人類食藥之源這個顯而易見卻被常常忽視的事實。地球上至少有五萬種植物可以食用(其中相當一部分也可供藥用),但人類歷史上被培育成食物來源的僅約7000種;時至今日,作為食物來源的植物只剩一二百種,而且作為食物主要來源的植物更是少至幾種——60%來自水稻、玉米、小麥。這可不是值得樂觀的趨勢:完整的生態系統及其原生生物的多樣性能減少傳染病的傳播范圍,但現在許多有利于凈化環境或可為人類醫藥開發利用和食用的生物并未受到應有的關注;“食源食物的野生近緣種正在衰退”,其中五分之一瀕臨滅絕,而人類本可利用這些“野生近緣種”培育出更為強健的作物。
科普書的詩意與哲理
當下,科普著作敘事在遵循學科細分與多學科融合的同時,大多十分注重話語的文學化、詩意和哲理性,這在三本書中不乏其例。
如《花花草草救了我》描述病人不得不面對巨大傷痛,而花園的象征寓意起著重要治愈作用時寫道:“果園里被截掉樹梢的老甜栗樹總是引得她的病人津津樂道,他們有時會說,想爬到粗大的樹樁上,想象自己坐在那兒,周圍簇擁著重新生長起來的樹枝。這些截頭樹是活生生的存活的象征。它們遭受了砍伐,經歷了挫折,卻找到了繼續生長的辦法。這些負傷的軍人也一樣,他們也必須設法讓自己修復、成長。”
《神奇生物的力量:大自然如何悄悄愛人類》在說明荷葉為什么能“出淤泥而不染”的原因前先描摹了出水蓮花:“它的莖挺立出水面,把葉子和淡粉色的花朵舉到雨中,離水面半米。這創造出一個水中版本的童話森林……落在荷葉和荷花上的雨滴,只是反彈開來。它們像亮閃閃的銀色球一樣在葉子上翩翩起舞。”作者贊美紅豆杉屬的物種經由紫杉醇成為治癌良藥,給許多人帶來了新生命,緊接著深情地設問:“如果我們能保護好它們,這世上的紅豆杉還會在我們耳邊低聲傾吐多少秘密呢?”字里行間流淌著汨汨的詩意與愛。
《地球之肺與人類未來》強調護林的緊迫性時寫道:失去這個星球上完好無損的巨型森林,數百萬種生命形態會消失,“而人類則會成為一支更加整齊劃一的兩足動物大軍,在一塊越來越死氣沉沉的巖石上狂歡。”“植樹是一種精神行為,是一種給予生命、確認親屬關系的祈禱儀式,它讓人們立即切實地扮演起看護人、家長和保護者的角色。”這不是故作驚人、故弄玄虛之語,而是包含著哲思、有震撼力的醒世箴言。
對這樣的表述,受眾樂于入眼,易于入腦,在常識基礎上,輕松地從感性的體驗上升到理性的認知,這也是優秀科普著作帶給我們的閱讀愉悅感之所在。
- 2023-08-07追尋空中花園在地球上的痕跡
- 2023-08-04從“教育問題”到“人本身” 石一楓《逍遙仙兒》新書發布
- 2023-08-04全國導游人員資格考試系列教材出版發行
- 2023-08-03《治大國若烹小鮮:引領新時代的36個妙喻》新書首發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











